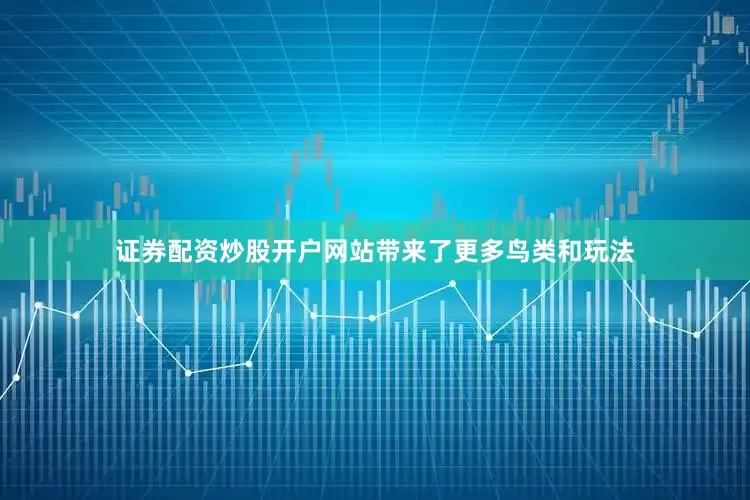图片
中国古代文献记载中的“律学”陈应时中国自古以来非常重视对于生律法的研究,並把这种研究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为“律学”。中国古代的律学研究成果,除了散失的以外,都被记载在中国古代文献之中,並向我们表明:中国的律学有其自身的发展历史,也有其自身的民族特点。一、古代中国人对于“律”的认识“律”就是用某种生律法产生出来的乐音:生律法所产生的乐音系列就构成某一种“律制”。中国古代很早就把一个八度分成十二个半音,称之为“十二律”。对于十二律的起源,《吕氏春秋·古乐》(前239)有这样的记载:公元前两千多前,中国的皇帝曾命令乐官伶伦作律。伶伦在昆仑山边取竹节,按凤凰的鸣叫声制十二律,並以两节间长度为三寸九分的竹简作为“黄钟之宫”(C)的标准高度。但从迄今的考古发现来看,在公元前16世纪起的商代和商代之前的乐器(如骨哨、埙、编磬等),它发音数由两三个至六七个不等,还不能奏全十二律。因此,伶伦作十二律之说,含有夸张的成分。但传说本身说明了上古时期的中国人已经认识到:乐音的高度可以用律管来记录和保存,而且可以用一定长度的律管来制定音阶的标准音。中国古代的历代王朝就是用律管的形式来制订和颁发“黄钟”(C)律标准高度的。律管的传说导出了古时期的“同律度量衡”学说,这一学说,被记载在相传为孔丘(前551—前479)编订的《尚书》中。这里的“首”是指记录和保存乐音高度的律管;“度”是指物体的长度;“量”是指物体的体积或容积;“衡”是指物体的重量。这一学说之所以把“律”置于首位,因为律管本身有长度,管体内有容积,管中所蹩之物又有重量,故“律实际上包含了度、量、衡。据此,许多文献记载都认为度、量、衡起源于“律”;“律”是度、量、衡的先导,是智慧的结晶。中国古代把十二年作为“一纪”,十二月为一年,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戍、亥)为一昼夜,这正好和律学中把十二律作为“一均”(一个八度)相合。因此,古代中国人把音乐看作象天体一样的自然之物,就采用数学手段,象计算天文历数那样,寻找各自认为最合自然法则的律制。中国古代文献中自《汉书》(约80)起就把律学和天文历数的计算合在同一个篇目《律历志》)中加以记载。二、十二律和“三分损益法”古代中国人在乐音体系中发现十二律之后,曾给每一律起了一个名称,即:黄钟(C)、大吕(#C)、太簇(d)、夹钟(#d)、姑洗(e)、仲吕(#e)、蕤宾(#f)、林钟(g)、夷则(#g)、南吕(a),无射(#a)、应钟(b)。这十二个律名最早被记载在约于公元前5世纪成书的《国语·周语》中,书中记录了公元前522年周代官州鸠答周景王问律的话,其中提到了十二律的律名。这一记载是可信的,因为1978年在湖北省随县出土过一套编钟,这是在公元前433年被埋入地下的遗物。这套编钟共64件,每钟可发二音(42钟各发小三度音程,22钟各发大三度音程),音域达五个八度,中音区具十二半音,证明了《国语》所记载的十二律,在那一个时期里确实已经在音乐实践中得到了应用。关于生律法的记载,最早见于春秋时代管仲(卒于前645)所传的《管子》一书,此书的《地员》篇中说明了如何用“三分损益法”来生律。所谓“三分损益法”,就是先将发音体的长度三等分,“三分损一”,即舍去其三分之一。取其三分之二(1x2/3=2/3),以生其上方的纯五度音:“三分益一”,即增其三分之一,成其三分之四(1x4/3=4/3),以生其下方的纯四度音。《管子》设“宫”(do)的律数为3⁴=81,先“三分益一”,再“三分损一”,生律四次,得五律: 3⁴=81(官,do) 81(三分益一)x1/3=108(徽,sol )108(三分损一)x2/3=72 (商,re ) 72(三分益一)x1/3=96 (羽,la) 96(三分损一)x2/3=64 (角,mi )由于用“三分损益法”所生的五律已构成五声音阶,所以《管子》的律学计算只止于五律。但仅此五律的律数不符合十二律的需要,故《吕氏春秋》(239)在《管子)生五律的基础上,继续用“三分损益法”再生七律,合为十二律:图片
《吕氏春秋》虽然记载了如何用“三分损益法”生十二律,但没有象《管子》那样标明每一律的律数。因此,汉代刘安(前179~前122)主持编写的《淮南鸿烈》曾尝试用《管子》所定的81为黄钟(C)的律数(其生律法改用先“三分损一”生上方的纯五度音),但发现在第五次生“应钟”(b)起就得不到整数的律数,所以又另立了3¹¹= 177,147为黄钟(C)的律数;这样,其所得的三分损益十二律数就全成整数。以外,司马迁(前145~前89?)的《史记·律书》在计算三分损益十二律时,采用了分数的形式。他设黄钟(C)的律数为1,则其他十一律的律数全是分数。用“三分损益法”产生的律制在中国就称“三分损益律”。这种律制的基本原理是和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律”(Pythagorean intonation)相通的,所以有些学者也称中国的“三分损益律”为“毕达哥拉斯律”。但仔细比较,两者还是有区别的。由于“三分损益律”采用“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的生律方法,所以只造成了向上方纯五度、向下方纯四度的生律结果。“毕达哥拉斯律”以向上方纯五度或向下方纯五度生律,因此,其“五度圈”中的十二律除了六律与“三分损益率”相同之外,其他六律是不相同的。请看下面〔表1 〕的对照:图片
由上表中的比较可知,在“三分损益律”中的变化音都带升记号,“仲吕”律也只能是#e。“毕达哥拉斯律”因可以由C生下方纯五度的F,转位后成f,其他变化音由此都带降号(b),故两者同样的七声音阶中,其第四度音就有#e和f的区别。这就表明了“三分损益律”和“毕达哥拉斯律”之间不能划上等号。三、京房60律和钱乐之360律据《后汉书·律历志》(约430)记载,汉代京房(前77~前37 )发现了上古时期相传的“三分损益律”有缺陷,因此又用“三分损益法”继续生律,直至第六十律,故后世称之为“京房60律”。在京房之前,三分损益十二律已经有了明确的律数,从各律的律数可以推定它们之间的音高关系,但这些律数转化为发音体的具体长度时,究竟以律管的长度为准则,还是以弦的振动长度为准则,这在当时並没有被明确。京房认为律数所代表的相对长度不适用于律管,而适用于弦。因此他造了一台形制如瑟的十三弦定律器,称为“准”,以作为他的律学实验工具。京房发现了三分损益十二律中的“仲吕”(#e)再“三分益一”所生的律(#B,他定名“执始”)回不到黄钟(C)本律〔177,147x(2/3)⁵x (4/3)⁷=174,762(2/3)〕,它们之间有差距〔177,147-174,762(2/3)=2,384(1/3)〕。这个差距,我们今天称“最大音差”(Ditonic comma ),其音程值为23.5音分(四舍五入作24音分)。在中国,这个音差当推是由京房首先发现的。此外,在京房之前已经有《礼记·礼运》一书中提出的“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的理论,亦即在音乐实践中要求实现转调。但京房认为,单用三分损失二律就不可能实现把十二律依次作为宫音(do)的转调。京房的这一发现也是正确的,因为三分损益十二律只可能包含五个相同结构的七声音阶;若以仲吕(#e )为宫音(do) 组成音阶时,则其他十一律中无一律可用。京房为了解决上述的两个问题,故又用“三分损益法”继续生至第六十律,並把这六十律的律度标记在他的十三弦“准”上。《后汉书·律历志》详细记载了“京房60律”每一律的律数以及由律数转化的具体长度。“京房60律”中黄钟(C)的律数沿用《淮南鸿烈》所立的177,147,在第五十三次“三分损益”所得的一律(京房称之为“色育”),其律数为177,147x(2/3)²³x(4/3)³⁰=176,776,和黄钟律数仅相差371。这个音差,京房当时称作“一日”(意思说,这个音差就好比一年中差一天),我们今天称它为“京房音差”,其音程值为3.6音分。由“色育”跳续“三分损益”生至第六十律的七音组成七声音阶,称“色育均”;它和最初由“黄钟”所生七音组成的“黄钟均”七声音阶,各个相对应的音之间都相差“一日”(3.6音分)。请看〔表2〕:图片
据上表,京房认为在六十律中基本上可以实现“周而复始”的转调了。京房发现了三分损益十二律的缺点,从而又把一个八度再细分为六十律,这在中国律学史上是一项创举。他的律学研究成果被他之后的学者们所继承。据《魏书》(555)记载,公元494年,北魏高闾曾奏本皇帝,建议推行京房的六十律和用他的十三弦“准”来调律;公元519年,北魏陈仲儒亦奏本皇帝,再次强调用京房的六十律“准”作为乐器调音的依据。他们的奏本都得到了当时皇帝的批准。但真正继续和发展了“京房60律”的是南朝的学者钱乐之。据《隋书·律历志》(636)记载,南朝宋元嘉(424~453)时,钱乐之在“京房60律”的基础上,又继续用“三分损益法”生至360律,最终的一律称“安运”,其律数为177,147x(2/3)¹⁵⁰x(4/3)²⁰⁰=88,479.14,更接近于黄钟的高八度177,147x1/2= 88,573.5,两者仅仅相差94.36。这个音差,钱乐之仍称之为“一日”,我们今天称“钱乐之音差”,其音程值为1.845音分。它比法国拉莫(Jean Philipe Rameau,1683~1764)在1726年发现的“小微音差”(Semicomma minime)1.954音分还要小。至此,“钱乐之360律”已经把“三分损益法”还生黄钟本律的音差缩小到最小程度,而且在中国律学史上到达了把一个八度细分的最高程度。此外,钱乐之把他的360律的每一律作为“一日”,故在三分损益十二律之间的“日数”依次为:黄钟(C)34、大吕(#C)27、太簇(d) 34、夹钟(#d )27、姑冼(e)34、仲吕(#e)27、蕤宾(#f)27、林钟(g)34、夷则(#g)27、南吕(a)34、无射(#a)27、应钟(b) 27至安运(C¹)。这就把三分损益十二律的十二个半音,从“日数”上分出大小,34天者为大半音(Major semitone),27天者为小半音(Minor semitone)。钱乐之把34或27律组成的一个半音称为“一部”,很显然,这十二部中有大有小,正合于我们今天对于古代的“三分损益律“存在大半音、小半音的理论分析,仅仅是表述方式上有所不同。对于这一点,过去似乎还没有引起学者们的注意,因此,钱乐之在律学史上的这一贡献也就被忽视了!“钱乐之360律”在古代几乎被失传,幸好有其后将近一百年的律学家沈重(500~583) 的追述,故得以在《隋书·律历志》中被记载了下来。四、“新律”和“新法密率”在钱乐之的同时代,律学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学派。据《隋书·律历志》(636)记载,南朝宋时的何承天(370~447 )不同意京房采用加律的方法来解决三分损益十二律不能还生黄钟和实现周而复始转调的问题,而主张在十二律内部加以调整,于是又创立了一种新的解决办法。经他调整的十二律后世称“新律”。何承天“新律”的律数全部记载在《宋书·律历志》(488)中。从这十二律的律数来看,何承天首先计算了仲吕(#e)再“三分益一”所生之律的律数为:177,147x(2/3)⁵x(4/3)⁷ =174,7622/3,它与黄钟(C)的律数相差〔177,147-174,762(2/3)= 2,384(1/3)〕,然后他把这个差数十二等分,递加在“三分损益法”每一次生出的律数上,则第十二次仲目还生黄钟时正好补上不足的律数2,384(1/3),吕还生黄钟的律数回到177,147。这样生律的结果,不仅解决了仲吕还生黄钟的问题,而且使调整后的十二律很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十二平均律”(Twelve tone equal temperament)。请看〔表3 〕:图片
类似何承天对三分损益十二律作内部调整的做法,尚有五代时的王朴(905~959)。据《旧五代史乐志》(974)记载,公元959年,王朴在十三弦“准”上制定了可以转七个调的十二律,并规定“黄钟”律道八度音之弦长为“黄钟”的二分之一。但王朴和何承天一样,因基本的生律方法仍然是建立在“三分损益法”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就调不出完全合于十二平均律的十二律来。到了公元第十六世纪的明代,科学家朱载堉(1536~1611)终于在总结前人律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计算,他称这种律制为“新法密率”。朱载堉发现了三分损益十二律之所以不能还生“黄钟”本律和实现象天体运行那样“周而复始”的转调,因为“三分损益法”用“三分损一”产生的五度音程太宽,用“三分益一”产生的第度音程太窄。于是在他的《律历融通》(1581)中首先公布了改变“三分损益法”的新方法:把“三分损一”(1x2/3=2/3)的分母缩小,即把一变成500000000/750000000,然后成500000000/759153538,这样,原来的“三分益一”就成了1000000000/749153538。朱载堉用这两个数取代了“三分损一”和“三分益一”,並仍沿用“三分损益法”的生律顺序,取得了“仲吕”还生“黄钟”本律的结果;其所生的十二律,即今之十二平均律。在同书中朱载堉还公布了另一种反生法,即先由“黄钟”生上方的四度音“仲吕”,再由“仲吕”生下方五度音“无射”,如此往返生律,最后由“林钟”还生“黄钟”本律。其方法:生上方四度音时乘500000000/667419927;生下方五度音时乘1000000000/667419927。这样生律的结果,其十二律也一样是十二平均律。朱载堉在《律吕精义》(1596年作序)中又公布了另两种“新法密率”的生律方法:(1)由“黄钟”(C)连续小二度生律至“黄钟”的高八度音“黄钟半律”(C¹),每次乘500000000 /529731547;(2)由“黄钟半律”(C¹)连续小二度生律至“黄钟光律”的低八度音“黄钟”(C),每次乘1000000000/943874312。图片
朱载堉在《律吕精义》中详细地开列了用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十二律律数;为表示其精确起见,每一律的律数都长达二十五位数字(不足者小数点后补以0,如“南吕”后有两个0)。有了这些律数,当然可以派生出前述各种各样的十二平均律生律法来了。
朱载堉在完成十二平均律数学计算的同时,在《律学新说》(1584年作序)中又设计了一台以实验他“新法密率”的十二弦“准”,他称之为“均准”。“准”上的十二,弦代表十二律,在“准”的面板上,中间设有按十二平均律计算出来的标记,並以此和“三分损益律”的律度作比较。按照准面上的十二平均律标记,在“准”上可以调出十二平均律的定弦来。
这里,对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的年代尚需作补充说明:朱载堉为《律历融通》一书作序的日期是公元1581年2月6日。这表明在这个日期之前朱载堉已经完成了十二平均律的数学计算。但他在此书中未详列计算公式,仅在书中写道:“其详则见诸《律吕精义》云”。由此可见,《律吕精义》完成于《律历融通》之前。因为在公元1595年旧历8月朝廷向朱载堉征诏律书,故朱载堉就将已经完成的《律吕精义》作了修订,才于公元1596年1月29日作序。因此,朱载堉发明十二平均律的时间,应该算为公元1581年2月6日之前。
五、琴律和《十则》从《管子》的“三分损益法”到朱载堉的“新法密率”主要采用数理方法来制订理想的律制,但中国古代也存在着由音乐实践本身所产生的律制,这便是“琴律”。“琴律”就是古琴音乐所用的律制。古琴,又名“七弦琴”,在中国古代又称“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拨弦乐器之一。古琴在乐器构造上具七弦十三徽的形制,这在汉魏时期(前206~公元265)已经确立。湖南省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汉初古琴有七弦,在枚乘(卒于前140)的《七发赋》和嵇康(224~263)的《琴赋》中都提到古琴上有徽。现存最早的古琴文字谱《碣石调·幽兰》系梁朝丘明(494~590)所传。谱中,七弦十三徽都用到,证明那时的古琴和现在的古琴在形制上已完全一致了。古琴上的十三徽是按照在琴弦上能奏出泛音(Overtone)的位置而确定的;它们自古以来被作为在琴上调弦和取音的依据。这十三徽的次序,按中国古代的习惯是自右而左排列的。一条弦在十三徽上所发出的泛音,正好构成了大三和弦的音响结构:图片
古琴十三徽所构成的音响结构为古琴音乐采用纯律(Just intonation)音阶创造了条件,我们从早期的古琴谱(如《碣石调·幽兰》、《广陵散》等)来看,那时的古琴音乐确实是采用了纯律音阶,因此,对于琴律的研究也被中国古代的律学家们所注意。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来看,《魏书·乐志》(555)中所载北魏陈仲儒于公元519年写的奏本中:已经把古琴五调的调弦法和“准”上的调律相提並论,但具体的调弦方法都没有记录,故还无从查考。到了宋代(960~1279),琴律已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了。在崔遵度(953~1020)的《琴笺》和沈括(1031~1095)的《梦溪笔谈》及其续篇《补笔谈》中,他们都注意到了古琴上发出的泛音,称古琴上的十三徽为“自然之节”,认为不论各种长短粗细的琴弦,都具有这种“自然之节”,在“节”上都能发出泛音,如果人为地改变这种“自然之节”的位置,就违反了自然规律,在琴弦上就奏不出泛音来。崔遵度、沈括的“自然之节”学说,直接导出了朱熹(1130~1200)的《琴律说》。在理论上明确地将琴律纳入律学研究范畴。《琴律说》概要地提到了自古相传琴工在古琴上确定徽位的方法,即所谓“四折取为中法”,据后来朱载堉的解释,这种方法就是把相当于琴弦振动长度的一条纸,依次折成二等分至八等(无七等分),取其“节”为徽的位置。据此,我们就可以知道十三徽之间的弦长比例和相对音高:图片
《琴律说》还探讨了按照徽位产生的古琴定弦法以及各条弦在徽位上所构成的纯律五声音阶音位。其五声音阶定弦的标准,以第一弦空弦为徽(S0l),第十三徽徽左为羽(La),第十徽为宫(do),第九徽为商(re),第八徽为角(mi)。这样定弦的结果就产生了纯率的五声音阶空弦音,仅其中的“第十三徽徽左”的具体长度不明确,没有确切的数的规定。因此,与朱熹同时代的作曲家姜白石(约1155~约1221)对当时的古琴调弦法作了改进,创立了一种更为精密的纯律音阶调弦法,他称作“侧商调弦法”。这一调弦法的调律依据是古琴上的第十一徽(4/5)和第十徽(3/4),要求左琴上的七条弦,每隔一弦不是和第十一徽按音就是和第十徽按音成同度,亦即每隔一弦不是纯律大三度(386音分)就是纯律四度(498音分),故就构成了精确的纯律五声音阶定弦:图片
古琴采用纯律五声音阶定弦,再按照合于纯律的徽位取音,就决定了左琴音乐的纯律性质。姜白石在制订了“侧商调调弦法”之后,还专门为实践这一纯律调弦法而创作了琴曲《侧商调·古怨》,在这首琴曲中还包含了纯律音阶的转调。中国古代的琴工从琴弦上发现了泛音,从而在古琴上设立十三徽,这只是对于泛音的一种自然认识。崔遵度在《琴笺》中提出“自然之节学说时,已经从理论上认识到了“谐音列”(Harmonic series)的存在。他认为一条琴弦上的泛音,最容易听到的有十三个,但实际上有二十三个,故可设二十三徽。可惜他在《琴笺》中没有作更详细的论述。至南宋时,琴家徐理于公元1268年写成的《琴统》书对谐音列作了具体的说明。此书中专设了《十则》一章,作者指出:“琴有十则,第四十五,同者十有四,得位者三十有一”。这就是说,在一条 琴弦上略去重叠的“节”不计在内,可以在三十一个节上发出泛音。于是作者沿着“自然之节”的学说分“十则”作具体解释。其第一则采用朱熹《琴律说》所定之全弦振动长度为四尺五寸;第二则将此弦长等分成二段生一个“节”;第三则等分成三段生二个“节”;依次类推,至第十则将全弦长等分成十段生九个“节”。在每一则中都详细说明了每一段的尺寸和各个“节”在琴上的位置。对照《十则》,我们可以知道,古琴十三徽只用了谐音列中的第二至第八谐音(缺第七谐音);崔遵度《琴笺》指出琴弦上有二十三个节,则发现了谐音列中自第二至第九谐音;徐理《琴统·十则》发现了谐音列中自第一至第十的全部谐音:图片
从中国古代琴工发现琴弦上的十三泛音,到《琴笺》、《琴统·十则》发现了更完善的谐音列,並在理论上加以系统的总结,这是中国古代琴家对琴律研究的结果,也是自然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件重要史实。对于这一史实,我想是应该充分加以注意的,因为它不是发生在科学发展的近代社会,而是发生在距今七百多年之前的中国古代社会里。从中国古代文献记载来看,古琴音乐的律制在公元第十七世纪时有了明显的变化。由于受古代传统的“三分损益法”理论的影响,沈括的《梦溪笔谈》、朱熹的《琴律说》都尝试在古琴上调出“三分损益律”的五声音阶定弦。因为古琴上的第九徽位处于全弦长的一,空弦的“三分损一”,正好是第九徽的按音;第十徽位置处于全弦长的一,以第十徽按音为基准,空弦音正好是它的“三分益一”。所以,利用这两个徽位,也可以调出“三分损益律”的五声音阶定弦。陈子敏《翠律发微》(1320)按朱熹《琴律说》所订的四尺五寸长(振动部分),计算了“三分损益律”音位与琴徽之差距;空弦为宫音(do),商音(re),在“十三徽外约六分七厘”,角音(mi)在“十一徽上约四分五厘”,徽音(sol)在“正九徽”,羽音(la) 在“八徽上约四分五厘”。这一计算是相当正确的。陈敏子又提出按上述一条弦上的音位来定琴上的七弦音高。以后,明代汪芝的《西麓堂琴统》(1549)、朱载堉的《律学新说》(1584)等亦都提倡古琴用“三分损益率”的调弦法。但从公元第十九世纪中叶之前的所有古琴谱来看,它们都仍然采用纯律高阶形式的记谱法。自从徐上瀛编的《大还阁琴谱》(1673) 首创“徽分”形式的记谱法之后,其后出版的琴谱均加以仿照,古琴音乐才被全面地纳入“三分损益律”的轨道。所谓“徽分”,就是将两徽间的长度十等分,每一分即一个“徽分”。有了“徽分”,古琴上除十三徽外,在每两徽间又都有了九个明确的音位。“三分损益律”音阶和琴徽不合的音位,就可以用“徽分”来标记。如空弦音的上方大三度音,纯律音阶按在第十一徽(4/5),“三分损益率”音阶则按在“十徽八分”(64/81),后者比前者高一个“普通音差”(Common comma,64/81÷4/5=80/81,22音分)。空弦音的上方大六度音亦如此,纯率音阶按在第八徽(3/5),“三分损益律”音阶按在“七徽九分”(16/27),后者亦比前者高一个“普通音差”16/27÷3/5=80/81)。综上所述,中国的琴律,实际上包含了纯律和“三分损益律”两种律制。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纯律的生律法(即调弦法)利用古琴上的第十徽(4/5)和第十徽(3/4);记谱法除记录徽位音外,只用相邻两徽名记录徽间的音位(如“七八”表示在第七徽和第八徽间间选择适当的音位)。“三分损益律”的生律法利用古琴上的第九徽(2/3)和第十徽(3/4);记谱法记录徽位音外,采用“徽分”形式来记录徽间的音位。中国的琴律尚有以下的特点:(1)利用古琴上的第十一、十、九、八、七徽,可以直接取得纯律高阶空弦音上方的大三度、纯四度、纯五度、大六度和八度音,在生律方法上比较简便。(2)古琴上有七条弦,琴面上无品位,故采用纯律定弦后演奏转调乐曲也比较方便。(3)琴律中的“三分损益律”与传统的《管子》法“三分损益律”稍有不同,因琴上有第十徽(3/4),“黄钟”(C)可直接生“仲吕”(f ),此“仲吕”是498音分的f,而不是《管子》法522音分的#e。所以,琴律中的“仲吕”(f),不论用“三分损一”(3/4x2/3=1/2)或“三分益一”(3/4x4/3=1),都可以回到黄钟本律。(4)琴律中並不局限于《管子》法只能生上方纯五度音或下方纯四度的生律方式,既可以利用第十徽生上方纯四度音或下方纯五度音,又可以利用第十二徽(5/6)生上方的纯律小三度音或下方的纯律大六度音;也可以利用第十一徽(4/5)生上方的纯律大三度音或下方的小六度音;等等。六、笛律和“异径管律”中国古代的律学,基本上都是以弦长作为计算依据,故诸律制的律数,一般都适用于弦律。律管的用途在于定标准音,在标准音确定之后,再用弦律计算,据弦律来定其他律管的音高。但中国古代文献中也有古代学者作管律研究的记载。据《要求·律历志》(约630),晋代荀勗(卒于289)曾制“十二笛律”。十二笛的管长严格按“三分损益法”计算,定“黄钟”(C)为九寸,“黄钟”笛之长为四个“姑洗”(e)之长〔9寸x(2/3)²x (4/3)² x 4 =28(4/9)(寸)〕,称“四角(mi)之长”,其他十一笛亦如此。但在笛上开六孔(一笛吹七音)时,荀勗发现,“黄钟”笛上的宫音(do)孔,不是距吹口为18寸,而是“黄钟”(9寸)和“姑洗”〔7(1/9)寸〕之和〔16(1/9)寸〕。这说明荀勗已经发现了管身的长度不等于管内空气柱振动的长度,因此要作“管口校正”(Mouth corroctiom),其校正数即“黄钟”和“姑洗”两律律数之差。他以这一原则制作了十二笛。但荀勗在开笛孔时用古琴作为辅助工具,因此,他的笛律仍然是建立在弦律基础之上的。明代朱载堉在发明“新法密率”的同时,在《律吕精义》一书中又提出了合于十二平均律的“异径管律”,以解决“管口校正”的问题。朱载堉从弦律研究中发现,弦上的不同音高变化,除了弦的长度不同之外,同样长度和松紧度的弦,若粗细不同,其所发出的音高亦不同。因此他认为管律除了注意管身长度之外,还必须注意管身的内径和外径。朱载堉对“新法密率”的管律提出了两种最基本的生律方法:图片
七、结束语中国古代的律学研究,走了大约两千多年的路程,在中国古代文献中留下了它的轨迹。在这个过程中,虽然由于出现了古琴这一乐器,导出了对于自然律的研究,发现了谐音列;也由于对律管的应用,导致对于“管口校正的研究;但从中国古代律学的总体来看,其研究的中心内容,是由于受到天体“周而复始”运动的启发,从而要求解决上古时期提出的三分损益十二律不能回归本律和不能“周而复始”旋官转调的问题。至公元第十六世纪末叶,明代朱载堉发明了“新法密率”,终于圆满地解决了上述遗留问题。朱载堉发明的“新法密率”,在当时的中国並未得到推广,因而对当时的音乐生活没有产生影响,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朱载堉仅仅提出了一种十二平均律的理想和具体的实施方案。幸好经欧洲学者们的努力,朱载堉的十二平均律理想,终于借助于键盘乐器而得以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实现,连中国也从西方引进了这种原本为本国学者早已发明了的律制,现在也已广泛应用。在上一个世纪里,英国音乐学家埃利斯(A.E-llis,1814~1890)在比较诸民族的音阶时。首创了音分制。这种把一个八度分成1200音分的制度,是根植于十二平均律基础之上的;就好比钱乐之把“京房60律”发展成360律一样,埃利斯把十二平均律发展成1200律,从而可以用这种音分制来量度各种各样的律制,把平均律理论推向了顶峰。然而我们知道,欧洲的传统音乐基本理论和五线谱记谱法,是建立在“毕达哥拉斯律'的“五度圈”(Circle of fifths)基础之上的;这个“五度圈”,也象中国的“三分损益法'那样,在理论来说是无穷尽的转动,永远不会“周而复始”这样的音乐基本理论在音名、音程、调号等方面实际上是不适用于表述平均律理论的。为此,当今音乐学者面临的一个任务,就是如何协调或解决传统音乐基本理论和新兴的十二平均律理之间所存在的矛盾。现在,十二平均律的音分制已经被国际音乐学界普遍接受。用音分制来描述各种律制的音阶,其误差度到达了人类听觉已不能分辨的1音分以下,因此,十二平均律及其音分制实际上已经取得了主宰音乐基本理论和改善目前无精确定量的五线谱记谱法的资格,按“五度圈”建立的音乐基本理论和五线谱记谱法,应该退居于从属的地位。根据中国古代律学研究的历史经验,以十二平均律理论取代“五度圈”理论的地位,这也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我们音乐学者应该为完善十二平均律理论体系而作出更大的贡献,让我们为此而共同努力吧!(本文为作者应邀参加澳大利亚音乐学会第十一届年会作演讲的中文稿——编者)……图片
作者简介:陈应时(1933—2020),男,上海人,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中国音乐史学家、古谱学家、乐律学家。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股票资配公司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 上一篇:配资信息网配资后面还有中端机、入门机等
- 下一篇:没有了